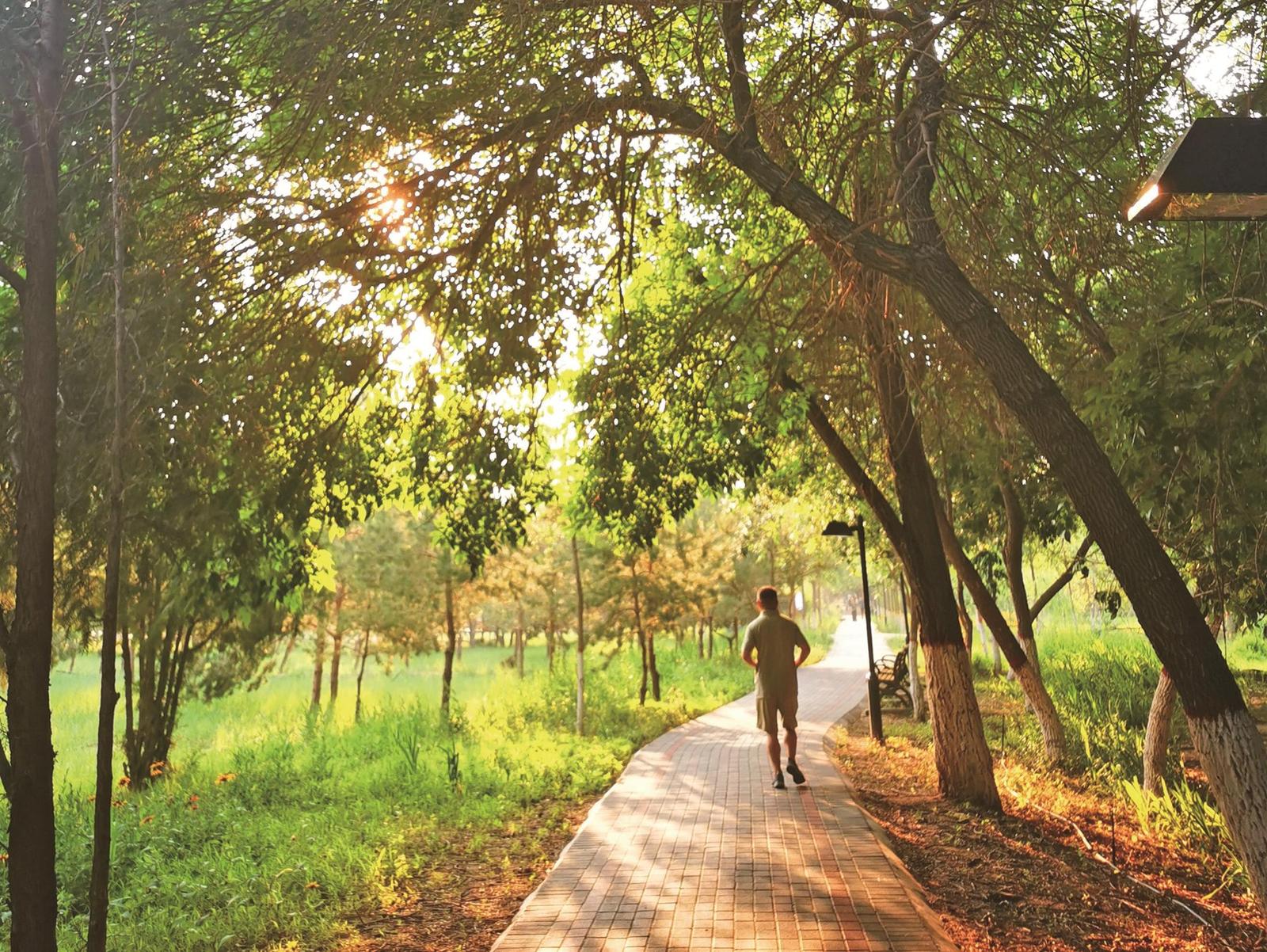
我到现在也还是没想起来他的姓名。到底叫什么啊……啊……
早晨上班,在公园小路的拐弯处,与一老头擦肩而过,有点面熟,不禁多看了一眼。他眼睛的余光大概扫到了我的注视,转头,愣怔,继而头向后仰,双眼圆睁,一手指我,道:“你你你……你是那个……勉会玲!”
“杜!杜!”我笑着说,一边拉下脸上的防晒口罩(我总觉得与人说话戴着口罩就像戴着手套跟人握手一样,有失礼貌)。
“哎呀,对、对,杜会玲,我怎么给记成勉会玲了。”他又是弯腰,又是摊手,又是跺脚,脸上的表情仿佛经历了悲欢离合后的重逢,充满了惊喜交加。
可是,他叫什么名字啊?哪怕想起个姓也行啊,我起码可以礼貌地称呼他一声,张哥李哥。
是我们单位的退休老头。感觉至少有二十年没见过他了。
只好嗯嗯、啊啊:“是啊,我还记得你说过的,你俩儿子小时候,你不给人家买雪糕,他们跟在你后面喊你小气的事。”我说。
“是是是!哈哈哈!”他仰头大笑。
可是——他到底叫啥名字啊?
随便聊了几句。无非是,都还好吧,现在住哪儿?孩子多大了?爱人呢……他告诉我,“孙子今年都高考了!”
“啊哦!”我惊讶地叫了一声——可是,我知道他是谁,我却不知道他叫啥。
阳光下,他脸上的老年斑像出土的青铜剑的铁锈,触目可见。头发白多黑少,没怎么谢顶。气色很好,人也和三十年前一样,不胖不瘦。
我还记得刚上班时,见习期间,我在办公室任打字员。那时候单位所有材料都是手写。手写好材料,拿到打字室,交给打字员打印出来。打字室是里外套间。里间是打字室,有两台苹果电脑,两台针式打印机。外间是油印机,各个部门自己刻蜡纸,然后两个人来油印,一人推滚子,一人揭纸。我还记得推滚子时,滚子滚过蜡纸时糯糯叽叽粘连的声音,像铺路时,巨大的铁滚子滚过沥青路面发出的声音。
为保密,打字员进入里间,要锁上门,无关人员不许入内。里外套间一墙之隔,墙上有个50厘米大小的正方形的洞,用于传递打印的材料。
可恨,还是想不起来他叫啥名字。
他那时候在一科。四十多岁,每有需要打印的材料,都是他拿来打字室,从窗口递给我。过半天,估摸着我打印好了,他再来窗口拿回去。拿回去还要校对,用红笔圈出打错的地方,再拿给我修改。修改材料时,因为时间短,他就趴在窗口那不走,等着。那时候刚上班,我总是一言不发,默默地干活,默默地交接打印的材料。
有一天,他在窗口外接过打印好的材料,满脸含笑地说了一句:“这姑娘真好,踏踏实实的,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(可是老天爷,我怎么后来变得那么爱废话连篇了呢)”
还是想不起他叫啥。
后来我去了财务,继续和他打着交道。他经常来报销本科室的差费,代领奖金。熟悉了以后。有次坐下聊天,他给我讲儿子小时候的故事。他有两个儿子。老婆没工作,他一人挣工资养活四口人,生活不宽裕很正常。夏天,他带两小儿出去玩。孩子看见卖雪糕的,要吃。他不给买。孩子纠缠,他不理,径直背了手在前面走。俩儿子跟在后面,一唱一和地故意大声喊:王岸真,真小气!王岸真,小气鬼!王哥说,他连头也没回,装没听见。
咦,怎么突然想起来了——原来他叫王岸真啊!
□杜会玲(宁夏银川)
